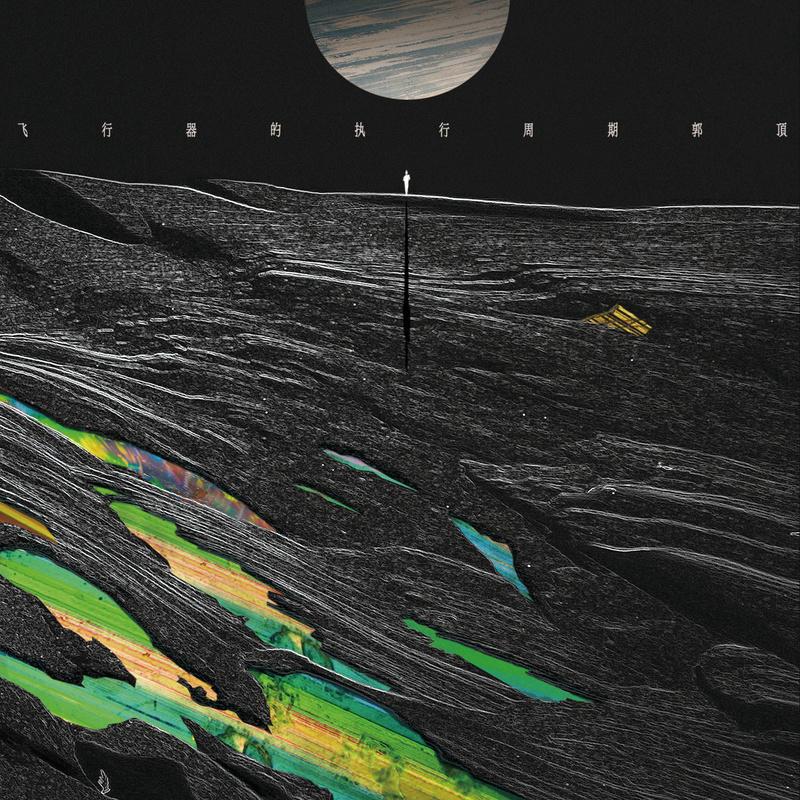
夏秋是果实和小孩子们一起成熟的季节。
果实有甜的酸的大的小的,人也有包容与刻薄、温柔与狠戾、清秀与粗野,等等。当然,这其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很久没有见到我的小朋友们,感觉真是突然就长大了啊。但不论如何脱胎换骨,我们喜欢的模样早已深深刻印在他们身上,两个人举手投足全都是少年的影子。
如此美好的存在,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坏。
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
闰六月总是不太寻常。这种不寻常有好有坏。莫名的事情发生太多,让人渐渐竟有点麻木的意味了。
某个炎热的夏夜,我下了晚课疲惫而饥饿地走在街上,准备到麦当劳打包一点夜食。推门正欲进入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劈头盖脸冲我骂了一句傻逼。我一头雾水地看了他一眼,他瞪着我咬牙切齿说“看什么看,你妈卖批”。我愣神之间只本能地觉得在外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一言不发从他身边走过去。店里的人一时都把视线聚焦在门口,我也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在关注方才那个男子还是听见了这番动静而好奇究竟是谁被骂了。如果是在平日我兴许还有耐性向店员打听几句前因后果;可在我早已身心俱疲时,连开口都显得太耗电(就像熬过通宵之后我常被人说面瘫,其实只是没有了做任何表情的力气),于是为哄自己开心而要了一对平时嫌腻不爱吃的鸡翅,除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多讲。
我的一个同学在首都某名牌大学参加化学竞赛夏令营时吞服氧化锌和浓盐酸自杀,未遂,住院几天后回了重庆,见到我连话也讲不出:舌头被腐蚀掉了。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以前是个太阳光的人,我总觉得我面前的这个抑郁症患者与他无法重合。然而事实就这样摆在面前,我只好无奈地看着他,他故作轻松笑笑,似乎口腔黏膜牵扯着疼(化学烧伤非常痛苦),总之这个勉强可以称作是“笑”的表情只维持了不足一秒。我想我是再也见不到以前那个人了,只好在心里默默说了声再见啦。然后我喂他喝了瓶牛奶,这是他的晚餐。他在医院挂水,我就择几本闲散杂志去陪他。他看了这期Vista讲《深夜食堂》的图,在手机上打字给我说很想喝夜啤酒,我白他一眼说你不是爱喝浓盐酸吗,他就惨淡地从喉咙里扯出委屈的笑声,然后打字说一点也不好喝。我只好叹气。我自始至终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件事。因为我看出他也不知道,甚至在这件事上比我更迷惑。
我家楼下一只虽然血统不纯但很漂亮的野猫,突然被摩托车撞死在路上。我想起前日里看见它在马路中间仰躺着晒肚皮时我似乎还对妈妈说了一些羡慕这些动物生活简单之类的话,有一点感叹,再加上一个朋友说起过老鼠药、环境污染对动物的威胁,就觉得:人对其他生物的羡慕或是怜悯有时未免主观得可笑。
长针眼了,奶奶说我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只好承认自己看见单元楼门口那只雄性哈士奇在墙根底下撒尿了。到医院看了,知道这叫睑板腺炎,说通俗点叫霰粒肿,拿了一支眼药回家滴着,倒也慢慢消了炎,只是留了个小印迹在眼皮上。
楼上有位老人过世,按我们这边的规矩在门前空地搭了灵棚、亲朋好友来搓麻将抹牌吃饭守夜。于是整个社区全笼罩在香火气味和哀乐的旋律中。年前上庙时寺里的师兄说我今年不宜去这些不大干净的地方,于是我日日绕道而行。
小区守门的那个瘦高男人出了车祸,肋骨断掉十来根,一根插进肺里,进了ICU这下就没那么容易出来;听说早已话都说不出了。我听了这些,心里只有一点茫然。这个姓张的男人给我的全部印象就只有沉默:他岁数很不轻了却仍独身,日复一日守着门口一个小副食摊,在年幼的我和姐姐递给他一些零钱买冰棍时、早晨匆匆出行的上班族买他的报纸时、深夜迟归醉意酩酊的人大声叩响铁门时,他都是那样一言不发。甚至在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时他也只是满脸漠然地随人潮走动,似乎对人们口中的灾难毫不关心。而如今他快要死了,我能想起的只有某次我从他手上买到的“七个小矮人”冰棍拆开只有六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拿了另一袋冰棍送给我吃。我听说他没有什么积蓄的,ICU病房的费用却相当惊人,而现在的医院在病人无法支付费用时是会立刻停止一切治疗的。
快死了的人还有我的姑父。姑妈去年刚癌症复发去世,姑父就查出胰腺癌晚期了。听到消息时我有点不太真实的错觉,甚至看见他瘦了五十斤、反复发烧面色晦暗我都没能消化这个事实;但当他说想出去散步却连家门把手都拧不动时,我才真的意识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生命一点点抽丝剥茧般离散,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在去年底过世的外公身上见过。旁观者亦不忍,何况亲历。
九寨沟地震时我在成都,震感相当明显。夜晚的街上涌动着人流,我没跟着走,在烧烤摊自己烤了两个串(老板跑没影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吃。我看着街上衣冠不整或穿戴齐整、神色惶恐或镇定如常、拖家带口或孑然一身的人们,想起汶川地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身边所有人似乎都突然变得极为热爱生命,锻炼身体保健养生的频率直线上升,然而过了约莫大半年,这些人再次开始出现在酒席与牌局上。我想真正热爱生命的其实要算我这种人,地震来了第一件事是下楼烤串,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其实我还想烤俩大腰子。
于是在这颇不平静的闰六月,一家人出门之前开始看黄历,路上遇见乞讨者开始慷慨地施舍,生怕一种叫做“时运”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不可抗的力量将我们的人生轨迹扭转了方向。
以上就是我胆小如鼠的生活。
偶遇了一场毕加索和达利的作品联展,毫不犹豫进去看了。以前不曾与他们的真迹这样近距离面对面,很多地方未尝领会,总觉这两人对待画笔的态度和对待女人一样:毕加索拥有过的五个女人,全都疯的疯傻的傻;达利钟情一人,数十年如一日。故而毕加索在我看来非常直接,而达利的画层次丰富笔触细腻色彩多变,一幅够我琢磨一整天。
看完这场展出我却觉得达利更容易理解了。这就好比不同风格的作家表达同样的内容,小说家的鸿篇巨著具体而浅显,诗人简单几句话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为达利的技巧叹为观止的同时,揣度推敲毕加索每一笔的用意也同样有意趣。
很多人对所谓“高雅艺术”总持排斥态度,其实大没有这个必要。例如我去看画展就只图个开心罢了,连相片也懒于拍一张,心里为这世上极美的事物而赞叹了,愉悦了,且也算是为艺术做了一点哪怕微不足道的贡献,也就实现了所有意义;我想毕加索和达利他们两位老先生也绝不会因为我这个观览者美术素养不够高而生气。娱乐虽然不是艺术的目的但可以是其反响之一,而一张画展的门票一百二十元,不及某些演唱会内场票的二十分之一吧。
这次的展品中有一组达利的青铜雕塑《时间的轮廓》,软化的金属时钟让人想到时间终究是种液体啊。
我不懂严肃艺术。不想懂,也不想严肃。
昨夜很迟了也没能睡着,就套上一件宽大的黑色连帽衫沿着锦江散步,凉意悠悠地从人字拖摩擦地面的声音里透出来了。这是成都的护城河,小时我常在坐在河边消夏,洁净而光滑的水藻在我脚趾间起伏游动,嘴里叼着汁液甘美的茅草根,手上捋着茅花柔软的白穗。我喜爱在水边生活过的作家,无论江海湖泊甚至哪怕是一口古井,在我心中水就是灵感。我喜爱沈从文汪曾祺曹文轩和所有用心描绘过水的写作者,有些人的故事里没有水,可水的哲学流动在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中。我的抽屉里躺着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了我小时候用茅花穗做的各种小物件,那是我读了曹文轩书里写用茅草花编鞋子之后收集最轻软洁白的穗子编织成的,质地如同鸟羽。我一生恐怕再也创作不出这样美的事物。
一路上看见零零星星死去的蝉落在树根,有的还挣动几下,发出虚弱的吱呀几声,随即也静下去了。终究是立秋过后了,夏日里最后一朵也是最浓艳的一朵玫瑰准备好了即将开放。最热烈的歌曲已经谢幕,能活到秋天的昆虫也开始排练自己的哀乐。秋主肃杀之音,我倒一点也不讨厌秋天,大概是死亡的气氛让人感到平静,而这平静对我来说多么可贵。
挺想和你们聊聊天,什么都可以。
有人在的话,就评论吧。

评论(23)